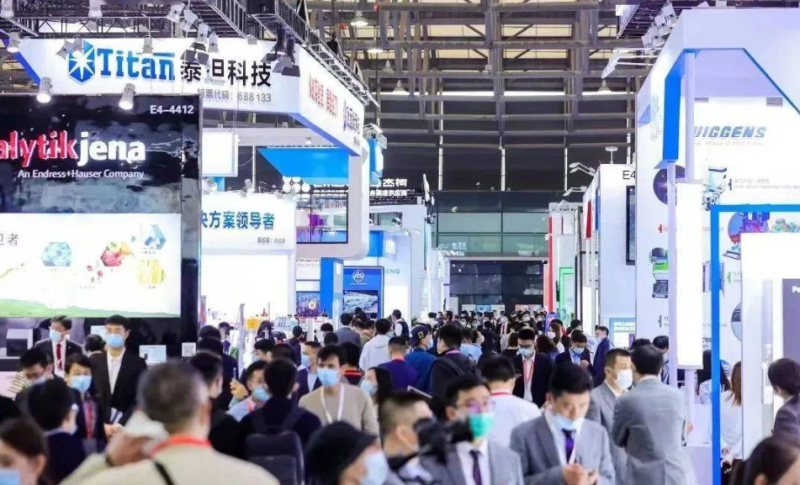方志是我国起源最早的史学形态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而且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血脉。正因如此,历朝历代,从官方到民间,对方志编修均极为重视,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志书。与之相应,方志编修理论也比较发达。
一、志书编修须融入新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方志编修尤为重视,专门成立了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统筹领导全国方志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就包含对于方志编修工作意义和价值的阐述。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指引下,新时代我国志书编修工作有了更大发展,在国家层面建立了方志馆,形成了覆盖全国、层次清晰、分工明确、体例比较严整的编修队伍和编修体制。
新时代的志书编修,既不同于古代时期,也与十八大以前的情况有所不同。源远流长的丰厚志书资源,在为后人留下一大笔优质资产的同时,也驱使新时代的志书编修守正创新,与新时代相适应,在扎实工作中有创新性发展,特别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体而微地贯彻进去,在建构新时代志书编修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强化顶层理论设计,编修出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型志书。
因此,方志文化在新时代应当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新的设计,使方志文化实现“活态化”“创新化”,进而融入新时代、链接新生活、创造新价值,自觉地与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方向相适应。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快速整体发展,志书编修与研究工作早已打破传统志书格局,视角已经从聚焦于乡村快速地扩展到城市与城市化发展上来,迅捷地载录了时代变迁中传统志书所不可能具有的内容。由于社会活动的丰富性、多样化,新时代志书必然要把以往所没有或不发达的各类现实囊括进去。这样一来,在内容扩展的前提下,志书编修的要素也必然发生变化,甚至载录对象的空间与时间单位都会发生变化,因而要求给出新的逻辑安排与框架定位。在遵守志书完整性、严整性的前提下,怎样使体例设计既能够突破以往的思维定式、扩宽思路和路径,又能够不坏规矩,与传统志书的优秀经验相衔接,将必有内容与新添内容有机整合,将内容载录与文旅产业相融通,将地域特点与国家整体统合起来,这对志书编修与研究都具有考验性。
二、志书编修须体现公共性
志书编修与研究是一种公共行为。编修志书是人类传承文明、存续文化、贯通历史的内在需要。志书编修者不仅在资料和社会之间居间说话,搭建起“理解”的桥梁,通过文本呈现,构建以社会为对象的公共产品,而且还搭建起今人与后人对话的桥梁。从本质上看,志书在人与人、现实与未来之间开辟出可共享的精神场域。当人们拿起一部志书的时候,内在地蕴含着从中获取确当知识以及清晰且有说服力判断的精神需求。在志书的两端,编修者、编修的对象以及志书的使用者,构成一个相互融合的共同体,公共理性活动由此而展开,志书文本由此而成为中心和枢纽。
志书所具备的客观属性,使其扩展出六个方面的价值维度。一是全面性,即志书所载内容具有应有尽有的价值维度;二是系统性,即志书对于内容的安排有体有用、体用结合,具有逻辑秩序;三是准确性,即志书载录不仅直书其事,而且能够做到事实与真实的统一;四是记述性,即志书以述而不作为特点,但内在地蕴含着以“述”为“作”的特质;五是资料性,即志书在史学系统中不仅被视为资料,而且是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因而为相关研究奠定基础;六是工具性,即志书具有备询查问的工具书功能。这六个方面,看上去很简单,其实都具有理论指向。
客观性无疑是志书的基本属性,它的指向是真实性。志书的真实性必须以再现的真实为核心,而不能让表现的真实喧宾夺主。所以,客观主义的“符合论”原则,是不可放弃的,尽管它还需要认识论上的严格检视。再现的真实也就是事实的展露,而不是事实的表现。但是,展露事实并不意味着没有创新性,不意味着这种展露仅仅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因为,展露事实是在一种叙述框架下进行的,这种叙述框架具有主题性。为了确保这种主题性,需要一系列程序来配合。例如,通过确定体例来体现设计上的要求,通过选择对象来体现内容上的要求,通过比事编排体现逻辑上的要求,通过文本呈现体现文体上的要求,等等。
这些工作,实际上体现了方志编修的创造性。由于这种创造性以客观性为前提,因此并不与真实性相违背。而且,志书的每一道工作程序,都有严格细化的要求,亦即“规范”。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客观性。
从志书的编修目标与最终应用来说,志书所体现的是公共性。可以这样说,以文本的确定性来规范阅读者的确定性,是志书的出发规则,也是志书性质所带来的认知基础性与核心理念。志书之所以不断地修纂,除实际需要外,也有不断修正和推进认知确定性的需求,从而为认识真理提供可靠路径。因此,志书必须体现公共理性规则,最大限度地为多种话语共同体所理解和接受。
志书的公共性体现为共享性。此共享性,不仅是共时的,即为同语境下的接受者所共有,并且是历时的,即为不同语境下的接受者所共有。符合公共理性要义的志书,可以为多数人所接受并反复经验,同时可以为历时阶段下多数人所共享。对包括历史和实践对象在内的志书产生出存疑的非确定性理解,终究要被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公共阐释所检验和确证。所以,所谓志书实际上是在公共理性的边界约束下所生产的可公度的有效文本。它具有相对确定的意义,且为理解共同体所认可和接受,并为深度文化传承和文明延展开拓广阔空间。
志书编修是居间性的理性行为。志书的生成、接受、流传,均以理性为主导。非理性精神行为是志书要排斥的行为,但精神性体验与情感意志无法完全也不需要从志书制作中排除,但必须经由理性逻辑的选择、提纯、建构、表达而进入志书制作。这是志书工作之所以可能的必备前提和实现要件。
志书文本是澄明性文本。志书编修将公众不需要直接面对的原始资料,加以选取、观照、编排、说明,亦即经过主体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过滤,最后使志书文本向公众敞开,渐次释放志书的自在性,即形诸澄明。志书文本的澄明是接受澄明、阐释澄明的前提。意在澄明的志书文本,是置入公共意义领域,为公众所理解的文本。
志书文本是公度性文本。文本的公度性是指,编修者与对象、对象与文本呈现、传授与接受之间,是可共通的。文本的公度性立足于公共理性建构的公共视域。认证公共视域的存在及其对文本传播的作用和意义,是文本得以公度的基础。公共视域是民族共同体基于历史传统和存在诉求的基本共识,是公共意见的协同与提升。文本的公度性是文本有效性的前提。
志书文本是建构性文本。志书编修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进程,对公众视域展开修正、统合与引申。志书工作不仅在寻求最大公度,而且重在于最大公度中提升公共理性,扩大公共视域。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志书文本超越并升华特定历史时段、特定领域视域,界定和扩大公共视域。这说明,志书编修同样具有教化与实践意义。
志书文本是超越性文本。志书编修超越于个体编撰。即使有个体编撰,也必须最大限度地融合于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在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的规约中,实现对自身的扬弃和超越,升华为公共阐释。志书文本的超越性,一是体现为对个体编修的超越,二是体现为对自己的超越。总之,志书文本的模型不是先天先验的,而是在不断的进步之中。
志书编修是反思性行为。志书编修不是纯粹的自我伸张,不允许强制对象符合己意,因此,它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在交流中不断省思和修正自身,以避免在实践中丧失原则。志书编修者既反思自己,也反思社会回应,校准和增补自身,保持自己的正当性、科学性以及工作的永续性,并以其公共效果进入历史传承。
三、载录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
最后,还需要讨论一下志书的载录功能问题。作为志书的核心功能,志书向来都是追求有意义的载录,也就是把各种事件都联系起来加以叙述。因此,载录也是一种叙述方式,意味着载录对象的固定化、秩序化和知识化。载录完成的时候,载录对象即被转化成为文本,其中凝结着志书编修者的立场、理论和思维过程。
甲骨文已经具有“记”的功能,用来记载甲骨来源、数量及祭祀等事项,还有对战功和狩猎擒获之事的记载。通过“记”,客观历史便转化成为“志”的题材,亦即将“事”(所指物)转化为“史事”(能指),由此而形成志书内部的三维文本结构:事、文、义。在这个文本结构中,“记”对于对象确定是决定性的,因为它实际上隐含着将所记录的事情固化为永恒的,也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历史流转不居,一旦被载录下来,也就被固定下来,因而成为知识的对象、主体选取的产物、叙事的内容、话语的话题。因此,从感觉要载录到实际载录下来,其间实际上经历了许多精神活动的过程。这些精神活动,代表、反映和凝聚了志书编修者的立场、水平和创造。因此,“记”也服从于立场和价值。
单纯的载录,只能是一种观念。凡载录,必有三个前提:记什么、不记什么,即抉择标准问题;怎样记、不能怎样记,即载录方式问题,包括格式、体例、体裁乃至文体等子问题。《史通·序例》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记”总是与“例”纠缠在一起,而“例”是文本组织与书写的核心事项。由上述二端,又引出第三个前提,即“记”的内涵针对不同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段,必有相应变化。
通常认为,“记”须“不隐”,实则未必。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做到对全部要素的不隐。当志书编修者给出载录对象的逻辑化、秩序化框架时,必然已经“隐”去许多。特别是在古代,“隐”或“不隐”必须符合“礼”的规范。所以,范文澜批评“孔子自己‘隐’,而称赞别人的‘不隐’”1。梁启超更是激烈地抨击《春秋》“恐其秽乃不减魏收矣”2。实则,董仲舒早就说过,《春秋》“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3。“杀”者,“渐降”也。又说:“《春秋》之书事也,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也,易其名以有讳也。”4“诡”者,“诡辞”也。一个“微”字与“诡”字,正反映了孔子的价值立场和选择标准。胡适为孔子辩护,说《春秋》中那些自相矛盾的书法,“或者不是孔子的原文,后来被‘权门’干涉,方才改了的”。但他也承认,“《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5。总而言之,从《春秋》的例子可以看出,所谓“述而不作”的载录,并不那么简单。
我们很有必要对所谓“记”,作内部结构的深入分析。《说文》说“记”是“疏”的意思,段注:“谓分疏而识之也。”6而“疏”,《说文》又说是“通”的意思。可见,“记”意味着“疏”“通”,非但不拒斥主体,还规定着主体的介入。只有沿着这样的向路去开掘,才能破解“记”的奥秘。我们认为,这样的开掘与“不隐”或“直书其事”的原则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可以提升我们对于志书编修的创造性的认识。
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卷,第53页。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83页。
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楚庄王第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19页。
4、董仲舒:《春秋繁露》卷3《玉英第四》,第127页。
5、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6、207页。
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许惟贤整理,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页,释“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来源:《中国地方志》2022年第3期
本文责编: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