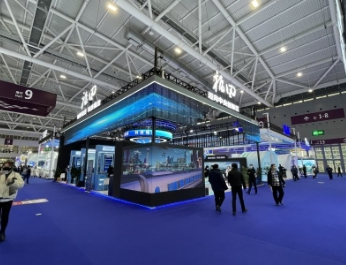编者按:千山之巅,万水之源,巍巍青藏高原,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孕育了万物生机。为揭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的组成,中科院之声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任务五“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联合开设“秘境寻踪”专栏,今天,我们将跟随中科院动物所科考人员的脚步,向地球的第三极出发,深入人迹罕至之境,探寻隐秘生灵,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守护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
负泥虫是叶甲家族里的一个亚科,数量较少,世界约有1000多种,中国有100多种。经济意义较大的有枸杞负泥虫、水稻负泥虫、百合负泥虫、薯蓣负泥虫等,而大多数负泥虫则是默默无闻(图1),经济意义并不明显。
虞佩玉老师是中国研究负泥虫的专家,20多年前,她把步甲类群交给我之后,就潜心做负泥虫、水叶甲、距甲的分类研究,编写中国动物志负泥虫卷。我野外出差,除了步甲外,见到负泥虫也收着,但只是偶遇所得,谈不上专门采集。
直到七年前虞老师去世后,我才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负泥虫。虞老师去世前的好几年,她的精力已经越来越不够用了,最终没把负泥虫那本动物志写完就走了,留下了遗憾。当我真正接触到负泥虫这个类群时,发现中国区区100多种,但问题还是不少的,也是年老体衰的老师很难写完的。很多模式没有检视过,有些物种连标本都没见到,个别物种的认知甚至来自原始描述那短短的三两行字,我觉得当时即使勉强写完出版,里面肯定会存在不少错误和疑问。

图1. 负泥虫和其寄主植物薯蓣(2020年拍摄)
2016年在法国自然博物馆,我特意去看了甲虫专家Pic的标本,然而该馆负泥虫标本很乱,找起来特别费劲,仅拍了几个种的模式标本照片,收获不大。2019年在大英博物馆,我检视了Baly和Jacoby的很多模式标本,收获比法国馆要大得多。后又检视了中山大学的模式标本,并索取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博物馆、瑞士巴塞尔馆、德国柏林馆、法国自然博物馆的一些模式照片。很感激的是,捷克同行Bezdek慷慨地把他多次访问欧洲标本馆拍摄的模式标本照片拷贝给我一份。这些年的模式标本检视,解决了不少疑问,我们对负泥虫的了解才日渐深入。
除了检视标本、索取模式标本照片外,我更乐意去野外,亲自去发现、观察和采集负泥虫。对生物学的了解、对寄主植物的掌握,是研究叶甲类昆虫的重要内容,而目前对许多负泥虫物种的认识仅仅建立在博物馆收藏的标本上,对其生物学一无所知。
虞老师生前很重视甲虫的生物学研究,她对河北张家口的谷婪步甲、对河北雾灵山的锯胸叶甲、对吉林长白山的两栖甲、对河南永城的白蜡梢距甲、以及对诸多铁甲和龟甲幼虫都进行了多年实地调查,解决了不少物种生物学、形态学和系统地位问题。但她对负泥虫的野外的调查则相对较少,或者说几乎没有。
2011年夏天,同行好友毕文煊在墨脱采集到一种负泥虫,送给虞老师鉴定。虞老师发现:墨脱这种负泥虫是一个新种,属于中国的一个新记录属——长颈负泥虫属。长颈负泥虫属原产印度,原来仅包含模式种一个种(图2),自该属发表后的100多年来,再无这个属的标本记录,也未有生物学方面的任何资料。幸运的是,2015年毕文煊在云南独龙江又采到了这个属的模式种,并拍摄到生态照片,很令人激动。

图2. 中国新记录属长颈负泥虫的模式种(原产地印度东部的曼尼普尔邦,收藏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2019年拍摄)
但是,我们对这个新记录属,特别是墨脱这个新种的生活环境和寄主植物知之甚少。因此,采集更多标本并记录其生物学成为我的愿望。发现墨脱负泥虫的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我带着三个学生去墨脱采集,寻找长颈负泥虫,从背崩乡到格林村的老路有七八公里,一路上山,很多地方泥泞难走(图3),外加上天气闷热,蚊虫叮咬,吃尽苦头。我们来回搜寻一天,没有发现此负泥虫。2015年至2017年,我又三次进入墨脱,但也没有收获。从毕文煊拍摄的照片看,长颈负泥虫的寄主植物是菝葜,但具体生活环境不甚清楚。此外,2012年之后,背崩乡到格林村开始修新公路,老路逐渐废弃不用,2015年之后便很难进入,我们沿大路采集,遇到的寄主植物都很少,负泥虫就更难见到了。
2019年启动的第二次青藏高原考察,我的任务是调查墨脱地区昆虫,继续采集这个神秘负泥虫的机会又来了。从格林公路到德尔贡,从地东公路到西让村,搜寻多日,虽然捉到了不少其他种类的负泥虫,但始终没有发现长颈负泥虫的踪迹。在野外,我经常面对林子,琢磨着它的生活环境,隐约觉得:这种负泥虫的个体大,但眼睛比其他种类小,应该生活在较隐蔽的环境内,若是像其他负泥虫生活在开阔地带,眼睛应该是正常的隆突型。

图3. 西藏墨脱县背崩乡到格林村的人马驿道(2012年拍摄,目前已经废弃,植物郁蔽,基本找不到路了)
2019年考察的后半程,我们从墨脱转战到了察隅,最后到了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我和队员们在马库村的老路上(图4)走着,观察着,期待着奇迹出现。就在这时,我面前突然有一只甲虫飞过,落在了一根芦苇枝条上,我便挥着昆虫网追过去,一下就扫到了网里。拿起来一看,这不是梦寐以求的长颈负泥虫么?太激动了,把虫子紧紧拿在手里,还怕失手飞走,匆忙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赶快收起来。
有了这个收获,激发了新的希望和动力,我们接着继续寻找,但再无第二只出现。遗憾的是,采到的这唯一一只长颈负泥虫还是在其飞行中抓到的,我们仍是不知道它的具体生活环境。这是长颈负泥虫的模式种,也就是好友毕文煊2015年在独龙江捉到而且拍到生态照片的那一种,而非墨脱的新种。

图4. 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马库村公路(右下角为长颈负泥虫,2019年拍摄)
2020年,我又去了墨脱和独龙江,在背崩乡格林村、江新村、地东村,搜寻多日,仍是没有发现长颈负泥虫。墨脱调查结束后,我又转战到独龙江乡马库村旧址,我总觉得,独龙江和墨脱有相似的温湿条件,植物和昆虫肯定也有着巨大的相似性。在马库村一处山坡上,我们新发现了一片菝葜,虽然面积不大,但比以前找到的零散单株好多了,我们在此处蹲守了两天,捉到了三种负泥虫,但都不是长颈负泥虫。
经过前面这六次的寻找,虽然屡屡受挫,但我对长颈负泥虫的渴望不仅没有消退,反而与日俱增、愈发强烈。2021年的春天,我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虑,5月份就带队出发了,首站就是独龙江,直接奔向马库村旧址的菝葜地点,一人蹲守负泥虫,其他队员在附近采集其他昆虫。我和学生及其中一辆车则继续扩大搜寻范围,在朗旺夺村,我们又找到了一大片菝葜植株,紧邻河边,既有向阳地点、也有郁闭环境,应该是适宜负泥虫生活的环境。我们还到马库新村——钦郎当,紧邻缅甸,但在那里找到的菝葜植株不多,有些“菝葜”植株后来请浙江大学的李攀老师鉴定,是薯蓣,并非菝葜。我们对寄主植物的辨认水平,还需要继续提高。
我们在马库旧址尽可能地扩大搜寻地点,沿着推土机新开的泥泞道路,向上前进,又发现不少菝葜植株,这是在独龙江乡发现的第三处菝葜丛了(第一处马库旧址,第二处在朗旺夺村)。下午,当我们返回第一处菝葜丛时,蹲守在此的司机张能见到我们马上大叫,“我发现长颈负泥虫了,已经捉到三头,快来拍生态照”,我们马上爬上土坡,到他跟前看个究竟。张能发现的三头都在菝葜丛林深处,菝葜叶的背面,很显然,它们不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我们尝试着拍生态照片,把捉到的一只又放回菝葜茎干上,但它总是躲着我们,并有展翅欲飞的动作,我们匆忙拍了几张角度不太好的生态照(图5),就赶快收了起来。
我们都很兴奋,从2012年算起,前前后后都十年了,终于又采到这个新种的新鲜标本,也初步掌握了它的寄主植物和生活环境。值得一提的是:司机张能这两年一直给我们开车,车停下就拿着昆虫网一起采集,经过2021年西藏墨脱采集、2021年3月的云南采集,他对负泥虫有了较深认识。派他值守这片菝葜丛,终于成功,是很好的证明。此外,他在云南哀牢山、通海阿依村、武定长己线,带我们找到了很多菝葜和负泥虫,我们很感激他。

图5. 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马库村菝葜和长颈负泥虫(右下角为墨脱负泥虫新种——虞氏长颈负泥虫,2021拍摄)
在独龙江采集到两种长颈负泥虫,其中长颈负泥虫模式种1头,墨脱长颈负泥虫3头,并初步证实了我早前的猜测,它确实生活在较隐蔽阴暗的地点。由于项目的主要任务在墨脱和察隅,我们匆匆离开独龙江,直奔察隅和墨脱,准备在墨脱寻找相似的环境,收获新的标本。
到达墨脱县的背崩乡,我们拿着两把镰刀,披荆斩棘,在当地护林员指引下,终于把格林老路(图3)找到了,并发现了大片的菝葜植物。在格林村边,还有另外一大片菝葜,也是比较郁闭的环境,有大树遮阴,也可能是长颈负泥虫的生活环境(图6)。这比前几年要前进了一大步,前些年我们只找到一些零星分布菝葜。2021年,我们拿着菝葜植株,找当地农户询问,找到了更多的菝葜集中分布地。因为菝葜嫩梢可以作为野菜食用,有经验的农户会留意菝葜的分布地点。而在大路边,由于菝葜藤条带刺,会刮伤皮肤,大部分枝条被当地人砍掉了。
在格林村,我们搜寻了四天,每天去菝葜地点两次,仍是不见长颈负泥虫的踪影,仅仅收获一些其他种类的负泥虫。虽然在独龙江采到了长颈负泥虫,揭开了部分谜底,但墨脱地区的长颈负泥虫在哪里?仍然百思不得其解。

图6. 西藏墨脱县背崩乡格林村的菝葜生境(右下角为菝葜果实,2021年拍摄)
2022年的春天来了,墨脱县背崩乡去年发现的两大片菝葜植株,应该又发出了新的枝条,梦寐以求的长颈负泥虫,今年会不会出现呢?从2012年至今,在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着一个场景:“细嫩的菝葜枝头,叶片正在展开,长长的须子,正努力向四周伸着,试图抓住其他植物,攀援上去;一只长颈负泥虫正抱着嫩条,徐徐向上爬行,时而啃咬着嫩尖,品尝着幼嫩的菝葜茎叶……”但这场景,只是萦绕在脑海里的一个幻想,只是一个梦,一个在墨脱尚未实现的梦。而这个十年长梦,应该迟早会实现的,也许就在今年。
来源: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